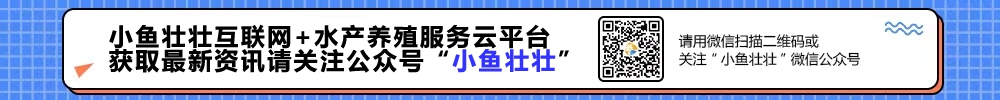鸟多了,鱼少了!谁来赔偿?
2017年11月,江西九江,一群候鸟在鄱阳湖自然保护区内越冬。 (视觉中国/图)
(本文首发于2019年5月16日《南方周末》)
“以前有外地人在附近的河里炸鱼,拦网捕鸟,候鸟不敢来。”2018年后,大丰当地政府严禁炸鱼拦网,候鸟多了,侵袭纪昌良家鱼塘的次数也骤增。
按野生动物保护法,野生动物资源属于国家所有,而现实中,补偿主体往往是地方财政。
水鸟吃鱼,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却让江苏盐城市大丰区的养鱼户纪昌良心力交瘁。2018年,他向银行贷款1000万买了鱼苗,年底却发现,养成的鱼还不及放下去的鱼苗多。他觉得,鱼儿都“喂”给了远道而来的候鸟。
乍看起来,纪昌良只能自认倒霉。但翻开野生动物保护法,第14条规定:“因保护国家和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造成农作物或其他损失的,由当地政府给予赔偿。”
除了野生动物保护法,《江苏省野生动物保护条例》第十七条亦规定,因保护国家和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受到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的,调查属实,县级人民政府应当给予补偿。
根据这一规定,通过料肉比估算——用所花费的饲料推算损失的鱼的价值,纪昌良向盐城市大丰区主管部门寻求2143万元的补偿。
不过,踏上索赔之路的纪昌良却发现自己成为又一个西西弗斯:从大丰区找到盐城市,再找到北京,最终又回到大丰处理,心心念念的补偿,依然遥遥无期。
这样的故事不只在大丰上演。在山西和顺县马坊乡,环保组织猫科动物保护联盟(以下简称“猫盟”)正在自筹资金,以补偿被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华北豹吃掉耕牛的村民。猫盟创始人宋大昭对中国野生动物损害补偿制度现状的评判是,“很少有地区在真正实践”。
鸟多了,鱼少了
盐城大丰被称为“麋鹿故乡、湿地之都”。全国唯一的麋鹿保护区坐落于此,每年10月起,沿海滩涂湿地还吸引丹顶鹤等大批候鸟前来越冬。
大丰人纪昌良今年64岁,从事养鱼已有30年。他从2010年起承包了大丰苇鱼养殖场的5个鱼塘,距离江苏盐城湿地珍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4-5公里。
候鸟原本与养殖场相安无事。2018年后,忽然多起来的候鸟成为纪昌良眼中的“大敌”。
“以前有外地人在附近的河里炸鱼,拦网捕鸟,候鸟不敢来。”纪昌良说,2018年后,大丰当地政府严禁炸鱼拦网,鸟多了,侵袭他家鱼塘的次数也骤增。
“2018年10月开始,每天清晨五六点,天蒙蒙亮,成批的海鸥、白鹭、鸬鹚(俗称鱼鹰)飞到我的鱼塘吃鱼。”他心急如焚,试过报警、打市长热线、点鞭炮驱赶,甚至想到了投毒饵。但大丰林业局的人告诉他,“伤害国家保护动物,会坐牢的。”
2019年2月,盐城电视台曾拍下候鸟光顾纪家鱼塘的镜头:一批鸟盘旋在鱼塘上空,有的在鱼塘里游憩。
根据纪昌良提供的视频,南方周末记者咨询的两位野保人士判断,正在吃鱼的可能是须浮鸥,位列IUCN(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红色名录,也是中国的“三有动物”(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受法律保护。鸬鹚、白鹭也是“三有”动物,白鹭属中的黄嘴白鹭、岩鹭还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动物。
候鸟来得最多的时候是12月,“1100多米长、700多米宽的鱼塘,密密麻麻全是鸟。”纪昌良很无奈。
纪昌良说,往年有六七十万斤的收成,债务不仅能全部偿还,还能赚三百多万元。结果2018年底,他总共只打捞出三万多斤鱼,两千多万元银行及民间借贷的外债无法偿还。他只能把银行来催债的人员带到“案发现场”,让他们体谅自己的苦衷。
有一定法律意识的纪昌良找到大丰区公证处“保全证据公证”。他提供的公证书里有大批海鸥在鱼塘捕食的照片,其后写着“与现场实际情况相符”。
纪昌良找到大丰区公证处“保全证据公证”。他提供的公证书里有大批海鸥在鱼塘捕食的照片,其后写着“与现场实际情况相符”。 (纪昌良供图/图)
林业局:调查仍在进行中
经过几次反映情况,2019年1月11日,大丰林业局前来调查。据纪昌良称,调查人员现场看到了候鸟侵袭。随后,由大丰(滩涂)海洋与渔业局牵头,检测了纪昌良鱼塘的水质。
据盐城电视台报道,大丰林业局给出的解释是,如果调查后能排除养鱼的水质、鱼类发病等因素,确定鱼苗大量减少确实只因为候鸟捕食,才能参照法规,“再来谈后面补偿的事”。
据盐城电视台相关人士介绍,在大丰,因野生动物损害自身利益而找政府要补偿,“几乎没听说过”。纪昌良养殖场附近的一名养鱼户也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2014年以来没遇到过大规模候鸟吃鱼的情况。
纪昌良的解释是,为了降低成本,他2018年采购的是草鱼鱼苗,而周边养鱼户则直接养殖成鱼。“成鱼有十几斤重,鸟不会去吃。我的鱼苗当时才长到每尾3两,所以成了候鸟的目标。”这倒与一位观鸟爱好者的理解一致,“须浮鸥捞不了很大的鱼,除非都是刚放进去的小鱼苗。”
受大丰政府委托,水质检测由江苏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动植物与食品检测中心负责。水质报告显示了331种农药检测结果,其中氰戊菊酯含量为0.25毫克/千克,超出了《河豚鱼、鳗鱼和对虾中485种农药及相关化学品残留量的测定(GB/T 23207-2008)》规定的0.05毫克/千克。不过,农药超标是否就是纪昌良鱼苗歉收的罪魁祸首,纪昌良并没有得到解释。
2019年5月10日,大丰林业局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调查仍在进行中。
野生动物损害补偿一直存在取证难的问题。“比如农民说野猪拱了我两亩地,想要赔偿,你咋去验证不是一亩半?”宋大昭认为,有的苦主会夸大损失,争取更多补偿。
取证的执行费时费力。中科院动物研究所工程师杨纬和认为,野生动物损害往往有高发季,如东北的野猪拱地、大雁吃稻谷,往往发生在秋收时节。“一天可能发生好几十起,范围也很大。吉林省以前规定,金额超过一万元的补偿要由省里的专家去做鉴定,专家一个一个去跑不现实,现在改成了超过五万元。”
中央和地方,谁来赔偿
“在补偿制度出台前,老百姓碰到野生动物损害的情况,都是自己‘解决’问题。”杨纬和说。
宋大昭记得,仅2017年,他们就收到54起豹子咬死牛的案例。如果没有补偿,故事有时会以悲剧收场:村民会在没被吃完的牛残骸上撒上毒药,回头再吃的豹子就被毒死。
其实,早在1988年第一版野生动物保护法就已经有了野生动物损害补偿的条文。1990年代末,国家就在西藏、云南、吉林、陕西四省开展“野生动物肇事补偿”试点工作。不过近20年过去,该制度仍停留在试点阶段。
巨额补偿金是地方政府沉重的负担。杨纬和注意到,自2009年开展野生动物肇事补偿以来,吉林省对野生动物造成的牲畜死亡给予市场价100%的补偿,农作物损毁给予60%的补偿,吉林省和珲春(县级市)财政各承担一半的补偿费用。但随着保护形势转好,野生动物损害的案例越来越多。“从2009年开始,补偿支出每年都在涨,单2016年,珲春市就为老虎吃牛补偿116万元。加上野猪、大雁取食农作物等其他情况,总共补偿达到365万元,这还不包括为了执行补偿工作发生的交通、人力等成本。”
2018年,当地就曾因为资金来源不稳定造成补偿款发放推迟的情况,因此还造成了社区居民对补偿制度的质疑,以及对野生动物的敌视。
能否提前做好预算?“野生动物造成损害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一般都是发生案例上报,再下发资金,很难有计划地去做预算。”杨纬和说。宋大昭认为,预算应建立在调研的基础上,国内对野生动物造成损害情况的调研还非常缺乏。
关键还是补偿主体的规定不明。杨纬和表示,按野生动物保护法,野生动物资源属于国家所有,而现实中,补偿主体往往是地方财政。
杨纬和观察到,在1990年代末试点工作开始之初,中央曾以专项经费的形式给试点地区提供一部分补偿经费,但是后来,主要都是地方政府在提供补偿经费了。
设立基金,联合保险
杨纬和称,目前国内只有零星的地方在落实野生动物损害补偿,多为亚洲象、东北虎等明星物种的栖息地,或是青藏高原这样的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除地方政府外,民间组织是设计补偿损害机制的另一大主力。
在三江源内的昂赛乡年都村,2015年户均损失4头牦牛,最多的一户达到27头。在这里,环保组织“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并未简单地出资补偿,而是由牧民、政府和民间组织共同出资组成“人兽冲突基金”。经过村民大会讨论,牧民给自家的每头牛投保3元,全村共投保25652元。
基金还确定了一条补偿规则:“如果发现牦牛被野生动物捕食是因为户主管理不到位,那么基金不予补偿。”由此强调了野生动物肇事是原住民和野生动物共同的责任。
即使有成功探索,资金仍是束缚。“猫盟”在山西保护华北豹的补偿资金,主要源自阿拉善SEE基金会的支持,数目有限。为了项目可持续运作,他们想尝试与保险公司合作,“猫盟”与村民各出一份保险金,为村民上野生动物损害险。
但保险公司觉得“不合算,没利润”,不愿承担这项业务;村民则觉得牛被豹子吃掉属于低概率事件,不愿投保。
“政府、社会公益资金介入,联合保险公司进行赔偿。”宋大昭依然在努力破局,“引入专业机构培训和评估,优化农牧业的生产方式,多方并举才能在生态保护和农牧民权益之间逐渐形成平衡。”
杨纬和强调,肇事补偿是冲突发生后的补救手段。“我们应该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前端,用于防范冲突的发生。”
纪昌良好像等不起破局了,“这次损失这么大,以后不会再养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