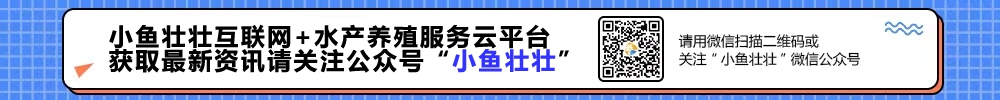元阳哈尼族梯田——好山好水开好田!还有“鱼
在云南南部,哀牢山中的先民们为了种植水稻,在陡峭的山坡上,用简单的工具开垦出了成千上万块不规则的小梯田。
云南的梯田,是中国最古老的人造梯田之一。我们的祖先也许没有想到,他们的子孙后代至今还在使用这种传统的耕作方式。这样的人造景观,是中国农耕时代最壮观的工程之一,远远望去,几乎每一寸土地都被用来耕作。
雨季的元阳梯田
“依山麓平旷处,开凿田园,层层相间,远望如画,至山势峻极,蹑坎而登,有石梯蹬,名曰梯田。”这是清代《建安府志·土司志》中对云南梯田的描述。梯田,是世界各地在山地耕作的农人普遍的选择,而哈尼族梯田把这种耕作方式发挥到了极致。据统计元阳哈尼梯田最多可达三千多级,坡度75°之高,这是世界梯田中绝无仅有的纪录。
哈尼族的祖先们用简单的工具,凭借智慧和毅力一点一点改变了哀牢山的景观面貌,在“地无三尺平”的陡坡上打磨出小梯田镶嵌的画作。这些小梯田的边缘,透露出高超的分割方法,线条沿着等高线分布,既节省人力物力,又最大限度地减小了坡面坡度,让小梯田形成一个水平面,把水围在其中,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水田。水田与旱地不同,对田埂平整度的要求很高,更何况是在高山之上的水田,在没有专业测量工具的年代,造田者们用灌水平田的方法,利用水形成的平面平整田地,就像哈尼族古歌里唱的那样:“水田挖出九大摆,田凸田凹认不得,哪个才会认得呢?泉水才会认得清。”
水,是梯田的命脉所在。高山拦截水汽的作用带来了丰沛的降水,而土壤隔水层的存在,使大量的水无法下渗,从而形成了丰富的浅层地表水,和在地表流动的小型水流。这种“山有多高,水有多高”的水土条件,使得在山坡上开垦水田成为可能。
水田沿着山脊层叠向上,不同于平原耕种的一马平川,这里耕种的是一个3D立体的水田体系。从河谷地带沿山脊向上,依次分布着河流区、梯田、居住区和森林,河谷低地的常年高温使流经的红河水不断蒸发,加上梯田水面巨大的表面积使局部蒸发量增加,大量水蒸气上升到高山森林区遇冷形成终年缭绕的云雾和降水,地表径流被收集输送到居住区,为村民提供日常用水,并将居民区中禽畜产生的天然粪肥冲入下游的梯田。梯田这个人工湿地是很好的净水系统,当这些水流入谷地的河流中时,粪肥等污染物已经被梯田拦截,不会污染自然水体;森林与梯田,又共同发挥着涵养水源、防止水土流失的功能。如此,梯田中就形成了一条良性循环的链条。
贵州东南部的梯田里,人们在为插秧忙碌
要驱动这链条运转,借助自然力量的同时,还需要配套的沟渠网络,一系列沟渠沿着村寨和梯田排布,这些沟渠的位置和分支经过巧妙的安排,能够将用水逐次送向每家每户和每块小田。梯田开到哪里,村寨建到哪里,沟渠就会修到哪里。
为了保证拦蓄的水资源在村寨和梯田中的合理分配,哈尼人创造了设计精巧、行之有效的“木刻分水”制度。他们在质地坚硬、水泡不易腐烂的圆木上凿出凹槽,放在沟渠的分水处充当分水器,控制每条支流的流量,也就控制了水的分配。每家每户、每块田每期的用水分配,由村民们一起商议决定,这之后“木刻”在制作使用中的一切事宜,就交给了村民推选出的“沟长”。关乎全村的生产生活,沟长的责任重大,因此沟长必须德能服众、公正无私,当然还要勤奋干练,因为他们的工作相当繁重,分水木的监制、安装和维修,沟渠的日常巡护、检查和疏浚,发现有人私自挪动或更改分水木时及时处置,维护全村用水的公平和秩序,都是沟长的职责所在。为了鼓励沟长尽职尽责,也为了补偿他们为公共事务耽误的自家劳作,沟长往往可以得到以稻米折算的丰厚报酬。
沟渠的流量控制功能不仅用于水量的分配,也承担着区域水流调节的作用,每当洪水来临,复杂的沟渠网络与层层铺陈的梯田一起,极大地减缓了水的流速,避免了严重的水土流失。这里山高坡陡,山洪、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频繁爆发。如今,哈尼人开田固田、开渠护渠的举动,在一定程度上让狂躁的自然力量变得温柔有度,让山崩地裂的咆哮变成了农耕时代的田园牧歌。
有了田和水,稻作便有了根基,但哈尼人的稻作智慧远不止于此。我们今天常见的粮食作物品种,相比传统品种,产量有了巨大的提升,这在造福人类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隐忧:在现代农业中,少数品种的大规模种植是普遍存在的情况,这带来了遗传多样性的丧失,我们正在渐渐失去传统品种中丰富的基因资源,而这些资源,正是我们改造作物品种的资料库。哈尼族的稻作却保留了另一种面貌:他们还在种植的传统稻米品种有百余种之多,可谓是一个珍贵的遗传资源库。
在水田中搞多种经营是南方常见的做法,元阳梯田也不例外。哈尼人在水田中养鱼,以鲤鱼、鲫鱼、江鳅等最为常见。他们在禾苗返青时投入鱼苗,到稻谷收获时恰好放水得鱼。稻田中生长的鱼在稻谷传粉的季节食花粉长大,有“稻花鱼”的美称。稻花鱼并非元阳独有,但稻花鱼争食跃出水面,落入下一级梯田,这种“鱼跳田”的景象,却是梯田中独有的景致。
除了哈尼人种植的水稻和放养的鱼、鸭,梯田里还有众多其他的动植物在此栖居,哈尼人接纳了它们的存在,使得这里成了生物多样性非常高的人工湿地生态系统。开辟了人工湿地的哈尼人作为这个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的要素,与其他要素保持着融洽的关系,让梯田延续着勃勃生机,哈尼人也从中获得了回报。哈尼人饮食中的蔬菜有相当一部分来自野菜,蕺菜(俗名鱼腥草、折耳根)、野慈姑、薄荷、水芹等都是常见的盘中餐;水田中的满江红、浮萍是绝佳的饵料和家畜饲料,与满江红共生的蓝藻具有固氮的本领,为稻田提供了良好的绿肥;昆虫、两栖类和鸟类也是稻田中的除害能手。梯田里的稻花、鱼跃、虫鸣、蛙声、鸟语……是梯田的喧闹,陪伴梯田度过千百年时光,也是梯田的宁静,由哈尼人世代守护。
两位哈尼族女性。哈尼族支系众多,服饰也各不相同。这两位女性来自云南红河州元阳县的一个哈尼族支系,年轻女性背孩子所使用的背带,和中年女性身穿的黑、蓝色调的上衣,都是传统的样式。
哈尼歌谣唱道:“有好山就有好树,有好树就有好水,有好水就开得出好田,有好田就养得出好儿孙。”如果说寨神林、村寨、梯田和河流是哈尼族农耕文化的血肉,那么哈尼人所创造的农耕传奇的灵魂,则是其中处处透露出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存智慧。2013年6月,红河哈尼梯田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作为农业文化遗产,哈尼梯田历史悠久、沿用至今,物质的梯田和景观、生态系统、种质资源,非物质的农业技术、农耕文化都被继承了下来。
借助现代的科学技术,我们对传统农耕中的智慧也有了更深层的认识,不再只停留在经验主义的规律和定性的关系上,我们了解了更多的内在机制和定量关系。然而依靠传统的农耕技术,能养活的人口毕竟是有限的,更何况高山地区的耕地资源并不充裕,随着社会的变迁,哈尼人也开始面临人口与资源、现代与传统的矛盾,对耕地的刚性需求使这里的生态环境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如何在改善哈尼人生活质量的同时,保护文化和生物多样性,是摆在今人面前的问题,寻求良策需要依靠现代科技,而传统智慧中天人合一的理想,或许就是解决这些问题的终极追求。
落日下的哈尼族梯田
哈尼族的岁首在农历十月,过年是庆祝丰收的节日,之后便是冬季的劳作,灌水养田,修整田埂,为来年的春耕蓄势。待到冬尽春来,哈尼人祭祀神林,祭祀祖先,摆开长街宴,迎接一年一度的“䀚玛突”——昭示着春天与新生的节日,节日过后,撒苗播种,又一年的春耕便开始了。阳光洒落,照见梯田的静谧;怒云翻滚,映出梯田的雄浑;霞光普照,投射梯田的奔放。梯田是变幻莫测的光影图卷,不变的是哈尼人劳作的身影,祖先的遗产、自然的馈赠,在四季轮转的播种和收获中不断演绎着人与自然共同缔造的农耕传奇。